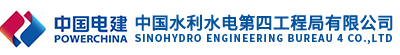獨憐幽草澗邊生 |
|
|
|
|
一旦過了烏鞘嶺,天地便陡然換了一副面孔。祁連山的雪線,像一痕清冷的白刃,直直地劈入眼簾。四圍是望不盡的黃土,干渴的、皺褶的山巒,一層疊著一層,仿佛大地凝固了的波濤。風在這里是唯一的言語,嗚嗚地吹著,帶著千年不變的蒼涼。就在這片被造化之手刻意雕琢得如此粗礪的天地間,我們的車,向著那更深的“澗”里駛去了。 所謂“抽蓄電站”,便是要在這亙古的荒寂里,借山為體,鑿石為腑,造一座深藏地肺的江河。那將是何等的幽深!我起初是不大能想象“幽草”會生在此處的。直到我看見了她們。 最先見著的,是開挖隊的勞資員。她的辦公室,是工地邊緣的一間板房,門前總沾著往來工友鞋底帶來的泥濘。我去時,她正被幾位剛下工的漢子圍著,空氣中彌漫著汗水和塵土的氣息。她并不高大,留著黑直齊肩發,像學生頭,坐在電腦前,卻自有一份沉靜。桌上攤著考勤表、工資單,還有一本翻舊了的《用工指導手冊》。一位老師傅嗓門大,對某個工時計算有疑慮,她便側著頭,耐心地聽,然后用帶著些許鄉音的普通話,一條一條地解釋,手指在表格上緩緩移動,直到對方眉頭舒展,憨厚地笑著點頭離去。那眼神里的信任,是這山澗里最質樸的認可。她轉頭對我歉然一笑,說:“都是離鄉背井出來掙辛苦錢的,賬,得給他們弄得明明白白,心才踏實。” 窗外是機器的咆哮,她這里,卻像是喧囂激流旁一處平靜的回水灣,用細致與公正,安撫著一顆顆懸著的心。我忽然覺得,這紛繁的人情賬目,便是滋養她的澗水了;她的堅韌,便在這日復一日的溝通與平衡中,如同澗邊滋養一方的青草,默默維系著這片小世界的和諧。 而后,是在那陡峭的邊坡上。巨大的山體被削成近乎垂直的立面,網格狀的鋼筋骨架已牢牢嵌入山體,如同為大山披上了一副巨大的鎧甲。就在這懸于半空的“鎧甲”之上,我看見了一群模板工。安全繩系在腰間,身影在數數米高的腳手架上移動,渺小得如同附于崖壁的甲蟲。自然而然的,我想到了一群精悍的、典型的工人形象。 直到,風毫無遮擋地刮過邊坡,比在平地更顯猖狂,安全帽下的亮色頭巾翻飛,而后又被扎進衣襟。定睛再看,竟有不少女工。其中一個正半跪著,與工友配合,將一塊厚重的木模板精準地卡入鋼筋網格。她掄起錘子敲擊調整,那“砰、砰”的聲響,在山谷間顯得格外清脆而堅定。陽光毫無憐憫地直射下來,她的額上、鼻尖沁出細密的汗珠,順著臉頰流下,滴落在干燥的黃土上,瞬間便被吸吮殆盡。我仰望著,那身影映在湛藍的天幕下,竟有一種雕塑般的凝重。她們不是刻板印象里的織毛巾的溫柔阿姨,用依舊用最原始的手上功夫,為這裸露的山體編織一件件遮風擋雨的“衣裳”。那一刻,我明白了,這最暴露、最無依的“澗邊”,恰恰是她們生命力量最直觀的彰顯。 拍完素材回程的路上,我又望向那莽莽群山。風依舊,蒼涼依舊。但我卻仿佛能看透那山石的肌理,看見其深處、其表面正有無數這樣的生命,在幽暗里扎根,在風日中挺立。她們不是招搖的喬木,也非嬌艷的花朵,她們就是這澗邊的幽草。核對工資時那專注的側影,女模板工在邊坡上那堅定的敲擊,樸素方言對面屏幕里那稚嫩的笑臉……她們與這雄渾而又冷酷的山河,形成了一種奇異的共生。 是的,獨憐幽草澗邊生。這“憐”字,是韋應物筆下“愛憐”與“惋惜”的雙重意蘊,是時間上的遲暮感與空間上的邊緣感奔涌交織。我憐的,是那份被粗糲環境所映襯出的、驚人的柔韌;是那種不與之爭鋒,卻默默與之共生,并最終要以自身的生命力將其點化的頑強。 敬意之余,心中亦生出一絲沉重。這千千萬萬生于“澗邊”的幽草,成就了時代宏圖的亦有“她”的堅韌,但她們的身影與付出,是否足以被看見、被銘記?當我們的目光追隨宏偉工程與壯麗數據時,是否也能俯身,去關注那些構成這宏大基石的、具體的“人”。她們需要的不只是被贊頌的堅韌,更是切實的尊重、平等的機遇和溫暖的關懷。她們的夢想,與腳下這片她們親手參與改變的土地一樣,值得被溫柔以待,值得擁有更肥沃的土壤和更明媚的陽光。 她們生于這時代的“澗邊”,也必將與這山河,一同不朽。 |
|
|
|
| 【打印】 【關閉】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