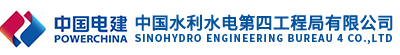我的第二個家 |
|
|
|
|
新疆的月亮總是帶著西北特有的坦蕩,大大咧咧懸在半空,大得好像塊銀盤,亮得能看清戈壁灘上每一粒石子,不像成都的月亮,總是躲在雨霧后,朦朧得像隔了一層紗。三年前踏出校園時,我以為自己會永遠(yuǎn)會懷念家鄉(xiāng)纏綿的小雨,涼絲絲飄在臉上,混著桂花的香味,還有街巷里火鍋翻騰的熱辣。卻沒料到,這片大漠戈壁的月光、風(fēng)沙與煙火氣,會慢慢織成另一個家的模樣。 初到項目的那個夏天,我還是一個連安全帽帶子都系不利索的“學(xué)生娃”。西北的風(fēng)很烈,陽光曬得人發(fā)昏,更讓人難受的是每日餐桌上那白花花的大饅頭,在家鄉(xiāng)吃慣了軟糯的米飯,面對沉甸甸的饅頭,總覺得噎得慌,每次一見著,必定苦瓜臉。那時的我不會想到,曾經(jīng)讓我犯怵的饅頭,會成為第二個家的味覺注腳。 三年時光,像戈壁上的風(fēng),吹硬了肩膀,也吹軟了心。 工作上,我早已不是那個需要師父手把手教的新手,如今能獨立完成崗位任務(wù),能單手把桶裝礦泉水從一樓拎到樓上辦公室,甚至能在風(fēng)沙里瞇著眼核對現(xiàn)場農(nóng)民工人數(shù)——西北的野,磨出了韌勁。 生活里,變化藏在一日三餐的細(xì)節(jié)里。曾經(jīng)讓我苦瓜臉的饅頭,漸漸吃出了門道:剛出鍋時帶著熱乎的麥香,掰開來氣孔細(xì)密得像海綿,空口吃都有淡淡的甜;放涼了切片,在平底鍋煎得金黃焦脆,往羊肉湯里一蘸,酥香混著肉湯的醇厚,比任何點心都美味。連食堂師傅都笑:“你現(xiàn)在變成西北人兒了!”其實不是饅頭變了,是心里的那道“墻”,被日復(fù)一日的麥香、羊肉的膻香、手搟面的筋道,悄悄融成了柔軟的接納。 今年雙節(jié),項目部比往常熱鬧了不少。長長的烤架支在院子中央上,那滋滋作響的烤肉、金黃焦脆的烤腸、鮮嫩多汁的蔬菜散發(fā)著誘人香氣,同事們分工協(xié)作:孫師傅經(jīng)驗足,負(fù)責(zé)翻轉(zhuǎn)食材,確保每塊肉烤得外焦里嫩;其他人負(fù)責(zé)調(diào)配醬料、端盤遞水、擺放桌椅,默契十足。 月光灑在院里的每處角落,落在每個人的臉上,大家圍坐在一起,舉杯共飲,分享工作中的趣事與生活中的點滴,沒人提工期的緊張、沒人說離家的遠(yuǎn),烤肉的煙火氣與輕松的交談聲交織,讓整個院子充滿了家的溫暖。老李舉杯時忽然感慨:“好像很多次中秋都沒有陪過自己的女兒了。但只要項目平安順利推進(jìn),工地成百上千名工人安全,也算給千家萬戶守團圓了。”話音剛落,滿座都舉起了杯子,碰在一起,叮當(dāng)作響,像在為這份舍小家為大家的默契鼓掌。 “新疆的月亮,是不是比家里的圓?”每次和媽媽視頻,她總是笑著問。我舉著手機轉(zhuǎn)了一圈,鏡頭里的月亮又大又亮,連月坑都看得清。成都的雨是軟的、纏纏綿綿,帶著桂花香;新疆的雨是硬的——下起來砸在鐵皮屋頂上噼啪響。可新疆的月亮,是“熱”的,清輝落下來,像剛出爐的馕,帶著股子實在的暖意。此刻忽然明白,月亮圓不圓,從來不在天上,而在心里——在同事遞來的半塊月餅里,在烤架旁默契的分工里,在饅頭掰開時細(xì)密的氣孔里。 鄉(xiāng)愁不是用來熬的,是用來釀的——把對家鄉(xiāng)的思念,釀成對“第二個家”的牽掛;把對親人的惦記,釀成對同事的關(guān)懷。就像大西北的拌面,剛吃時覺得不如家鄉(xiāng)的火鍋熱鬧,可吃久了,卻愛上了那勁道的面條裹著濃郁湯汁的實在,愛上了大家圍著一張桌子“加面”時的默契。 月光依舊灑在項目部的院子里,照亮烤架上滋滋作響的肉,照亮同事們臉上的笑,也照亮每一個堅守崗位的水電人心里,那片被煙火氣焐熱的、名為“家”的地方。 |
|
|
|
| 【打印】 【關(guān)閉】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