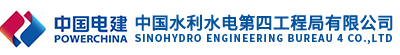當我們的筆,遇見他們的山河 |
|
|
|
|
從金塘沖回來已有些時日,但那段記憶卻愈發清晰。每當合上雙眼,大壩上忙碌的身影、機械的轟鳴聲、還有那份撲面而來的熱忱,都會重現眼前,恍如昨日。 記得那天,高鐵正行至湘鄂交界,手機屏幕忽然亮起。是引江補漢項目的金主任發來的消息:“小梁,剛看到你寫我的報道發出來了。每一段都特別戳人,讀完我愣了好久......”窗外的景色飛速掠過,我卻捧著手機反復讀著這段話。這段突如其來的肯定,洗盡了我連日的疲憊,瞬間覺得所有的付出都有了意義。 參與這次采風之前,我內心滿是激動與忐忑。作為一名新手,我擔心自己無法勝任這份工作。最初以為采風不過是收集素材、完成稿件,直到遇見孟令婉,我才明白文字需要怎樣的敬畏。她會為一個標點反復推敲,為核實一個細節不厭其煩地多方求證。“文字若是失了真,再美也是虛空,”說這話時,她的眼神專注得像在打磨一件傳世瓷器。從她身上,我學到的不僅是寫作技巧,更是一種對真實的執著堅守。 許靈均總是安靜地坐在角落改稿。她的電腦屏幕上總是同時開著十幾個窗口,一篇報道修改十幾遍是家常便飯。她不僅精心打磨自己的文字,還細心幫我們糾錯別字、調整語序。“這里再加個細節會不會更好?”她總是這樣溫柔地建議,讓每個人的文字都變得更有力量、更有溫度。 劉吉星則讓我見識了什么是“行動派的浪漫”。為了一個完美鏡頭,他能在烈日下待整個下午,飛無人機飛到幾乎中暑。記得那次無人機卡在樹上,金塘沖的任主任二話不說就爬上山坡幫忙尋找。陡坡碎石滑落,他險些摔倒,卻還笑著說:“你們記錄的也是我們的故事啊。”這句話,至今溫暖著我的內心。 最難忘的是那個雨天,98年的生產主任王棟棟帶著我在工地上穿梭。雨中的工地別有一番氣勢,他如數家珍地介紹每個施工環節,清楚記得每個工人的名字和崗位。雨水順著安全帽檐流下,他的眼睛卻格外明亮。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這座大壩為何能拔地而起——因為有無數這樣的年輕人,正將青春澆筑進混凝土中。 回首這次采風,最珍貴的不是我們產出了多少篇稿件,而是那些意想不到的溫暖相遇:我們的筆遇見了金主任珍藏的往事,遇見了任主任爬坡時滴落的汗水,遇見了王棟棟在雨中的堅守,遇見了孟令婉對文字的敬畏,遇見了許靈均的溫柔細致,遇見了劉吉星的執著追求。 曾經以為,水利工程是冷硬的鋼筋水泥;如今懂得,每一方混凝土里都攪拌著滾燙的人生。我們帶來的筆,寫下的不只是工程進度,更是那些藏在歲月里的堅持、那些不為人知的付出、那些值得被銘記的瞬間。 當我們的筆遇見他們的山河,寫的就不再是文章,而是遇見;不再是采訪,而是對話;不再是任務,而是生命的饋贈。 工程終將竣工,但我知道,有些東西會比混凝土更持久:金主任那句“借著你的文字,重新和過去的自己見了面”,任主任爬坡時留下的腳印,還有我們這群人在這個夏天共同寫下的關于真誠、專業與相遇的故事。 臨別那天,我們互道珍重,期待下次重逢。我也在期盼,期盼能繼續書寫更多四局的故事,四局人的故事。因為在這里,我遇見了最真誠的伙伴,最熱烈的追求,最負責的擔當。這段經歷必將為我的寫作注入不竭的靈感,成為我職業生涯中最寶貴的財富。 筆會停,故事永存。山河記得,我們記得。這份溫暖與感動,將永遠照亮我前行的路。 |
|
|
|
| 【打印】 【關閉】 |